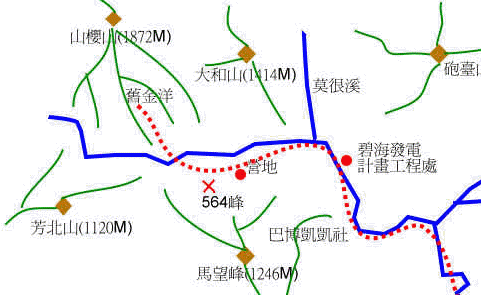老金洋尋根之旅92.3.13~3.15
| 踏著先民的腳步 我們尋找一種族人間濃厚的情感 縱橫於山水間 那是剪不斷的臍帶 峭壁間迴旋著祖靈的呼喚 來了!我們回來了! |
大家在出發前幾天一直祈禱著天氣可以好轉,因為我們三天的尋根之旅由澳花村旁的和平北溪上溯,若再繼續下雨,要帶著五、六年級的男孩渡河而過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好在天公做美,大家的虔誠讓我們可以如期出發。前蜂部隊是我們學校愛釣魚的總務主任勝雄和二名村裡的獵人,他們已在活動前一天動身前往老金洋要。 |
|
【孩子的期望】 「我希望這次去老金洋可以看到以前阿公、阿媽住的地方,去那裡看老金洋美麗的風景,雖然我們全班都生病了,智利昨天還去吊點滴……我們希望病趕快好,這是一個好機會,不去會很可惜……」 早上7點20分從金洋村坐著發財小貨車到澳花,蘇花公路上的砂石車呼嘯,不久就會更遠離文明,雖然我們本來就生活在群山中,但是老獵人口中如飛機場般大的河谷,山羊、山羌成群,溪中的苦花像手臂一樣長……老金洋的傳說與神祕讓我們更加期待能親眼看到老金洋的一切。 車過澳花村繼續前行往和平北溪採礦場方向進,這裡有幾條叉路分別到不同區域的採礦區,要取靠右往主要溪流的方向,這裡的通行道路都是開採砂石的廠商所堆挖出來的,漫天飛塵,可以想像每當颱風來時,濤濤泥水來襲的可怕。一路前行會遇到在溪旁的一小型開砂機,要不懷疑地從中間經過,順沿河床而下,不到2分鐘就到了下車處,眼前翻滾灰黑的河水從來來往往的砂石車中流到太平洋,忙碌的直昇機「咑……咑……」在我們頭頂迴旋著。風聲、河水夾雜著現代的機械聲,沒有一刻停歇的忙碌。 每個獵人背著傳統籐製的簍子(Kili)與長槍快速地上路,通常獵人是不背那麼多裝備與食物的,他們頂多背帆布、要吃的米,以前的老獵人會帶地瓜或香蕉飯。但這次的成員多了學校的老師與小朋友,所以金洋的獵人們更有使命地多背了沈重的帳篷、鍋具和一堆的罐頭。 在下車處即要往右橫渡到對岸的獵徑,此路徑經常有人經過,所以路跡明顯,兩旁紫花藿香薊帶來春天新鮮的氣息,約行15分鐘出小徑往左橫渡。河岸前方公路上儘是碎石傾瀉的山壁,即使覆蓋在山壁上綠色套網一點也彌補不了採礦後山壁缺塊的突兀。 |
|
|
|
【我們在三月來】 我們選擇在3月來,天氣較暖和,同時也避免梅雨季時河水暴漲,渡河不易。今天雨量算少,但涉水深度也深及臀部,金洋的獵人們一個人帶一個小朋友手牽手渡溪,孩子們興奮的心像白白的浪花,充滿原住民在山野裡的奔放。河谷往右轉折約步行約30分鐘後可見台電工程的流籠,一路渡河數次後約上午10:30分,學校裡唯一的在地老師,Loby告訴說:「以前這裡長了很多又粗又大的竹子,中間的河島就是太魯閣族與我們族人分界限,誰超過了,就會被砍頭……」歷世的物換星移,原來在這裡的竹林被一次又一次的大水沖毀,剩下的是芧草及苧麻科植物的台地,還有曾經在這裡令人血脈噴張的傳說。 過半小時,看到左側一大片岩壁上的噴漆字就要從此直上攀過巨石,大夥兒在巨石上休息,一位年輕獵人指著左側不遠處被溪水侵蝕一大半沈積台地說著「那就是山羊、猴子會出沒的地方!」孩子們睜大眼睛看著,真希望會有一隻野生動物從裡冒出來。越過岩區後是一小片的沙洲,跨過右邊被燒焦的漂流木,冰涼的河水冷卻了剛剛被太陽燒烤的酷熱。到了中午11:50分可見清徹的溪水蜿蜒地在右側溪谷裡,當然這裡就是我們午餐的地點,也是第一個匯流口,順著可愛清徹的小溪而上,有一個小小的深潭,孩子們就在上方的小瀑布上釣魚。吃完泡麵,很快就動身了,40分鐘後遇到一個已架設好繩子的橫渡點,石壁上噴著「大家加油!」的字樣,水流湍急。再過半小時經過一完整工寮,但無法在去程時一眼看到,不過在入口處有一棵很大的無患子長在石頭上,相傳以無患樹的木材製成的木棒可以驅魔殺鬼,沙地上滿地的無患子,Loby教孩子們如何用無患子洗手,只是這樣無污染的洗滌方式已顯少有人使用。 2:20分又遇一條支流,我們過此支流再沿著河階台地而上,續往右行,兩旁的大理岩峽谷迴然與一路的景觀相異,由河水深切大理岩層所形成的峽谷,宛若一道巨大閘門矗立在狹小的河床上,在過閘門後二十公尺處的右側山壁有一個蝙蝠洞,但現在已有沙堆幾乎堆滿洞口,也沒有任何蝙蝠。已3:20分,較常來的獵人警告我們不可在此停留,因為隨時會有落石,河道變窄,河水相對較急促,幸好現在是枯水期,大人們還可以站在波濤洶湧的溪水中協助小朋友安全渡河。 |
|
|
【莫很溪】 只約20分鐘我們就到了莫很溪。「這裡的水溫較高,所以苦花的顏色較白,下游的水溫低,所以苦花的顏色較深,不過它們一樣都很笨……」獵人哈勇–葉一邊把釣到的苦花塞到保特瓶,一邊得意地著說著。不到二十分鐘保特瓶就已半滿,有些肥美的苦花已經無法直接從開口塞進去,要開另一個小洞。這裡的溪水有些混白色,溪底是細細的黃泥,一過溪時就可看見腳邊四處游散的苦花群,從這裡上溯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到莫很溫泉,聽說溫泉是用噴的,而且上游的苦花更多,晚餐的魚有了著落,溪谷冷冽的山風催促著我們往營地出發。 到了獵人們口中的飛機場,這裡視野遼闊,寬約一公里的河谷,野生動物的腳印隨處可見,也是野生動物的天堂。馬望峰和炮臺山互相對望,獵人說這個大崩壁是日本人當時從炮臺山上用火炮轟炸結果,馬望峰大崩壁下的巴博凱凱社也早已被土石流所淹沒,以前的族人曾在這一片廣闊的河谷台地上耕種小米,不過大部分的居民還是住在山上的部落,來來回回的山路更增加了以前耕種的辛勞,尤其是婦女,若要照顧孩子還要背著小孩上山、下山。 下午雲霧環繞著溪谷旁的中級山,諾大空曠的河床上多了金洋子們的足跡與隨處可見的山羊腳印交錯著,幾個孩子互開玩笑地要問山羊是從花蓮來還是從宜蘭來。我們正走在土石流乾涸堆積的沙石台地上,一但下大雨這些堅硬的土塊將會變成「流動河床」。 564峰下的平緩溪谷是我們紮營的地點,只有小小一條不到一公尺半寬的溪水是我們主要的水源,平靜地幾乎感受不到它在流動。我們到了營地已是下午5點,獵人們早已熟練地升起熊熊烈火準備晚餐,此時卻飄著斜斜細雨,增添向晚涼意,一天將近六小時路程的疲備,孩子們在吃完晚餐後很快就累了,紛紛在帳篷裡東倒西歪的進入夢鄉,不知在這塊祖先們曾生活的土地上,孩子們會做什麼夢!不見月光,夜晚的篝火未息,一直陪我們到天明。 一大早獵人哈勇就忙著煮子米準備醃苦花,苦花在釣上之後用鹽醃過可以保持肉的彈性與甜味,小米只要煮到半熟再用冷水冷卻、擠乾就可以和苦花一起醃, 回去再放到罐子裡密封起來,約三、四天後就可食用。哈勇說:「從小我就喜歡跟著父母學習如何料理山上的食物,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很有趣。」醃好的苦花和冷飯一起吃,古老的口味真使人懷念! |
|
|
|
【尋找舊金洋】 濃厚的雲層重重的壓在群山間,為了安全起見,孩子們就到芳北山尾稜左側溪谷裡釣魚,山櫻山(1872M)和大和山(1414M)間的數條稜線上,就是許多舊部落的起源地,以前居民對外的主要路線是從這裡步行約三至四小時,到太平山分四段坐蹦蹦車到土場再到羅東。校長請獵人阿不拉帶我們到從前山上的部落,阿不拉民國三十八年生,一直到十二歲才離開這裡。我們從營地出發後約不到30鐘路程,往河谷右邊的一條稜線往上切,上切點的入口是一個河凹,有一個小沼澤在那兒。阿不拉詳細地描述以前學校的樣子,最先的校舍是由日本人興建,後來因為颱風校舍全毀,當時村長集合村裡的壯丁用竹子、芧草建立學校,連桌椅也是用竹子做的,村長的堅持讓這個離文明好遠的山上有一所學校,讓這裡的孩子可以繼續接受教育,更辛苦的是這裡的校長、老師們,平均一個學期才可以回去一次。所有的課本或老師要用的物品都是由工友耗費體力從太平山那兒背過來。阿不拉感嘆地說以前的村子向心心力強,不分彼此,很願意一起分工合作,但現在卻找不到以前的樣子,大家都各忙各的。 鹿野忠雄在【台灣原住民的鄉土觀念】中,就曾提泰雅族的土地,是為其部落所共有,而且有公有地和私有地之分,儘管是高山僻遠的不毛之地,也有其關係確立的所有權,至於土地的範圍,而且互不侵犯。 沿著稜線陡上,一路都有林務局植林的楓香樹,看見野櫻花的紅色果實一點一點地掛在翠嫩的枝頭,真令人驚豔。約二十分鐘就到了一個台地,這裡以前種地瓜,原住民會把土裡的石頭撿起來堆成一崁一崁的踣崁,除了整地方便耕種外,一方面也可防止豪雨所造成的土石流。山路崎嶇難行,我們走的路似乎是山羊的行徑,舊部的癈墟靜靜躺在平坦的台地,一層一層地沿稜線而上。茂密的蕨類幾乎把四周的遺址所淹沒,隨著獵人的腳步前行,我們找到比人還高的石牆,依舊矗立在這蠻荒的森林裡。此時就在不遠處傳來山羌的叫聲,這裡林木蒼翠、群山爭秀,曾經把數個部落孕育在與世無爭的自然中。 近午時分,我們望著對面遠山的稜線,老金洋就在上面,校長Haya實在很想上去,但因時間的限制,我們要和孩子們會合,只好心有不甘的作罷。Haya自從長大後就很少爬山,可以說是新一代泰雅族的文人,他開明的作風,讓我們有機會和孩子來這裡。阿不拉叫我們自己先下山,他則去尋找山羌的蹤跡,若是沿途有什麼狀況,或是迷路了,只要大叫他就會趕來了。好不容易下山卻找不到孩子們在哪釣魚,快到一點了,肚子餓得沒力氣,我們決定折返,後來遇到阿不拉才知我們走錯了方向,從下山處要往左側到他們釣魚的溪谷,路程約10分鐘就到了。狼吞虎嚥地吃完大家幫我們留的午餐,躺在河邊的大石上享受風濤流水,「啾!啾!」斯文豪氏赤蛙的鳴叫聲雖然向亮,也無法阻止矇矓的睡意。 今天的行程愜意,回到營地還沒吃晚餐,月亮很快的昇起,晚上8:00獵人們好像游擊隊,分組、分路線準備好整裝待發。由於安全上顧慮,孩子們在營地裡守火等待,四周漆黑,對岸的山谷裡,山羌的警告聲忽遠忽近。零晨12:30,還未見他們回來……這時我想到一首席慕容的山月 「我曾踏月而去 只因你在山中而在今夜訴說著熱淚裡 猶見你微笑的面容 叢山黯暗 我華年已逝 想林中次次春回 依然 會有強健的你 挽我拾級而上 而月色如水 芳草萋迷」 在帳篷裡伴著孩子們的酣聲,竟不知不覺睡著了。 白天和夜晚是情敵,白天獻出美麗的黃昏,希望大地不要將它忘記;夜晚在臨走前留下瑰麗的晨曦好讓大地記住。獵人不知昨夜何時回來,一大早個個已收拾好行囊,為什麼他們可以不怎麼睡覺,還能如此般精神抖擻。用過早餐後,禱告完畢,我們除了原來的背包,還多了3個大內胎,準備將所有的背包、獵物綁在內胎上順流而下運送出去,金黃的陽光灑滿整個河谷,我們好像一支滿載而歸的商隊,回程孩子們依舊精力旺盛,不過我們卻快累翻了。 |
|
|
【又是春天】 清新的綠意綴滿山谷,我們在新生的季節到來,可是我卻充滿了予盾與爭扎回去,更直接的說是充滿罪惡感;看見燃燒的垃圾,食物的殘餘在渺無人煙的乾淨溪谷裡,我讓自己成為「順應民情」的人。以前的獵人有嚴謹的狩獵原則,在繁殖的季節是不可以打獵的,剛出生的動物也不可以獵殺,否則會遭遇危險。狩獵的確成為部落裡一些弱勢群體維持生計的方式,我們很希望在這樣的活動裡,可以隨著獵人的腳步找回一些原鄉情懷及老獵人在山野裡狩獵的倫理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哲學,隨著部落結構的瓦解,這些似乎已被獵物所換取的金錢交易所取代,但確實有些人生計的維持為此。獵人的笑話:「反正動物遲早都會死,到不如就到我的肚子裡!」該怎麼傳承部落裡 |